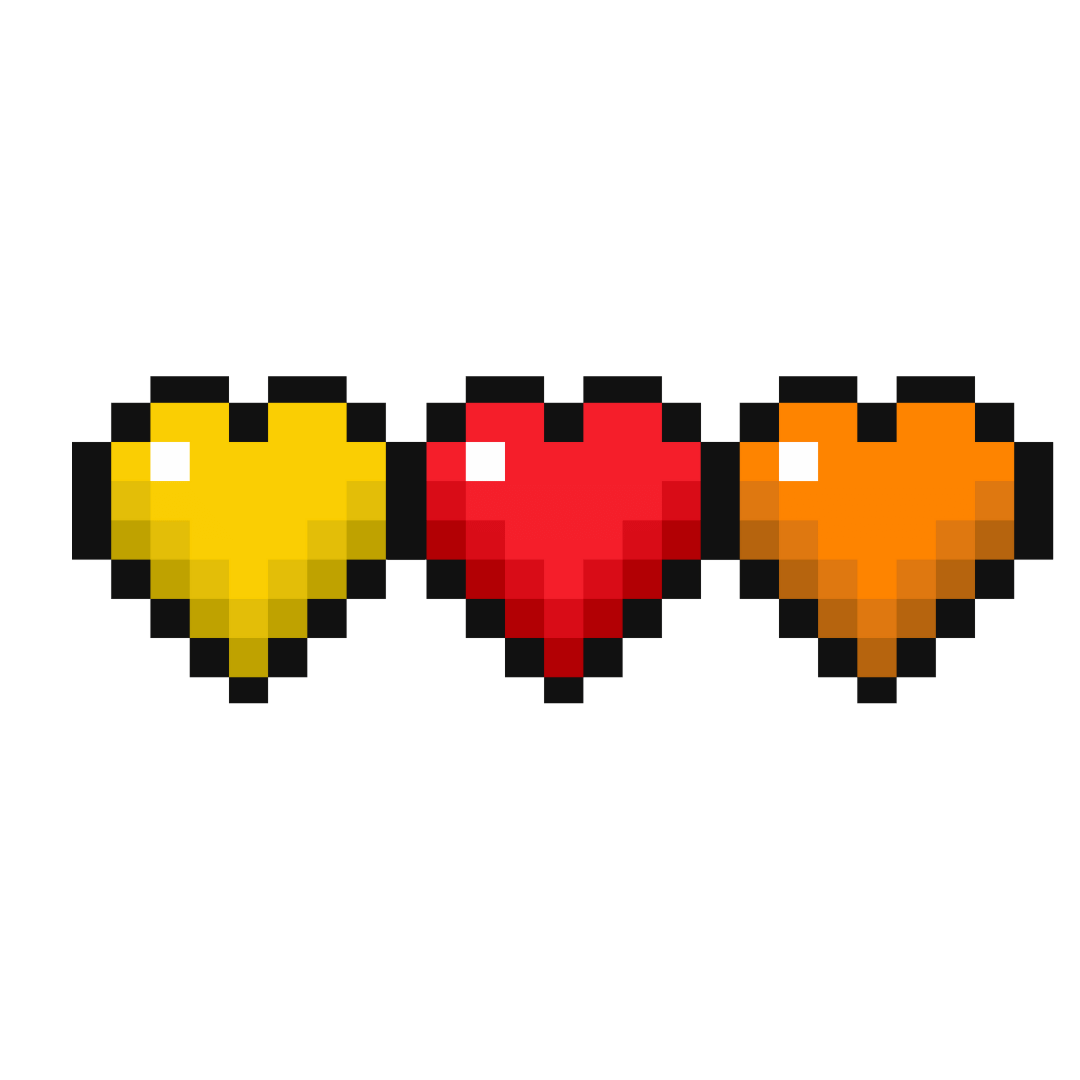這個時代,我們是誰─《亂民全講》 #

舞台劇的模糊美學 #
你有沒有試過用最新的4K螢幕玩二十年前的遊戲?畫面每一塊像素都粗糙顯眼。但如果你換回當年的CRT螢幕,就會發現角色變得栩栩如生。這是因為老舊的顯示技術帶來的模糊性,反而讓大腦主動補足細節,填入想像空間。

左為原始圖片,右為經CRT映像管電視顯示後的樣子。 圖片出處:CRT Pixels 📺 Twitter / CRTpixels
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:在影像技術如此發達的時代,為什麼我們還需要舞台劇?
常見的標準答案是:「因為現場表演的張力無可取代」、「因為舞台的即時性與互動性是電影、電視無法比擬的」。但這些答案講的多半是「演出本身」的差異,而不是真正屬於「劇場文本」的獨特性。
真正讓舞台劇與影視作品不同的,是 「模糊性」。這種模糊,來自留白的台詞、隱喻層層堆疊的敘事方式。它讓觀眾不只是觀看,而是參與解讀,成為文本的共創者。有人看得熱血沸騰,有人則滿腹疑問。這種不確定性,正是舞台劇的魔力。
而《亂民全講》,正是「模糊美學」的極致展現。
顛覆常規的政治寓言 #
2003年,表演工作坊推出了《亂民全講》,一部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的政治諷刺舞台劇。它的名字是對當年熱門政治諷刺節目《全民亂講》的戲仿,但與後者的短篇惡搞不同,《亂民全講》更像是一場結構嚴密、層次豐富的劇場實驗。
網路上仍可找到這部劇的完整片段,雖有版權疑慮,但這讓新世代有機會接觸這部經典之作。

點擊收看: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Yw1bFc63DE
這部作品的核心是對社會的深刻觀察與批判。「民主化」 一段尖銳地諷刺了流於程序的假民主;「媒體」 揭露了新聞的淺薄與操弄;「全球化」 講述了文化隔閡的荒謬與誤解;而 「國民監獄」 則點出高房價壓迫下的生存困境。令人震驚的是,這些議題在二十年後依然成立,甚至比當年更加沉重。這齣戲究竟是超前時代,還是我們的社會一直停滯不前?

但《亂民全講》的高明之處,並不僅限於直白的政治諷刺,而在於它同時隱藏了一條幽微的情感脈絡──那些似乎無法歸類的段落,如 「快閃族」、「身分」、「KTV」,講得似乎是情感,卻也不只是情感。表面上看來與政治無關,卻是對這個時代最深刻的精神映照。

當結局變成開場──戲劇語言的反轉 #
戲還沒開始,舞台燈光卻亮了,演員上台鞠躬,觀眾席響起事先錄製的熱烈掌聲。這場戲就這樣,以「謝幕」的形式開場。
這一刻,觀眾產生了巨大的錯愕──難道我錯過了整場演出?接下來會發生什麼?這種混亂感,預告了這場戲的顛覆性。它不是一齣遵循傳統敘事邏輯的作品,而是一場不斷挑戰觀眾的實驗。

亂序與重複:戲劇的拼貼美學 #
我對《亂民全講》的熱愛,除了它銳利的政治諷刺,還有它獨特的敘事結構──乍看之下是零散無序的短篇拼貼,實則是一場高明的編排遊戲,將不同片段交錯重組,形成一種有意識的「亂序」。
這種敘事手法,讓我想到許多作家創作時,靈感並不會線性降臨,而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,最後才回頭重新編排。這部劇也是如此,每一個段落看似獨立,卻透過精心設計的重複與對比,讓觀眾在不知不覺間,浸入了它的敘事邏輯。
 圖片出處:「于善祿 語言/精神分析視野下的《亂民全講》」
圖片出處:「于善祿 語言/精神分析視野下的《亂民全講》」
觀察它的場次安排,會發現某些戲碼並非一次性演出,而是被巧妙地分散在整場劇中,甚至呈現近乎對稱的分配方式。重複的堆疊,使得某些畫面與台詞在觀眾腦海中逐漸發酵──一次出現是一個意思,十次出現則成了一種強調。
此外,抽象隱晦的段落,往往被安排在語言直白、批判犀利的片段之間,形成強烈對比,彷彿讓觀眾在思考與感受之間來回擺盪。
沉默的快閃族:舞台上的休止符 #
其中最耐人尋味的,莫過於 「快閃族」。
這是一組幾乎沒有台詞的段落,演員透過肢體動作與音樂來表達,而快閃族1尤其令人玩味。當角色試圖對觀眾說話,便會被其他人「噓」下去。這種沉默與壓抑,與其他喧囂吵鬧的政治諷刺場景形成極端對比,像是戲劇樂章中的休止符。
而最巧妙的設計,是它在謝幕後的再次出現。
在觀眾以為一切都結束時,快閃族的演員依然站在台上,靜靜地看著觀眾離場。這個段落,竟然在觀眾的「退場行為」中得到了新的詮釋──我們以為自己是來看戲的,其實我們也是戲的一部分,正被台上的人觀看。
這與 「身分2」 段落遙相呼應。當那名自稱活在虛擬中的女性說:「你們以為自己是觀眾,但其實,你們才是演員。」戲內與戲外的界線早已模糊,舞台上演的戲,其實比現實裡發生的,還要更像現實。

快閃族的意象,貫穿了整部劇。 #
快閃族2 描繪即將分離的戀人,探討愛情與人際關係;快閃族3的投影則觸及戰爭與現實的殘酷。這部作品看似只在談政治,但透過快閃族的演出,它真正關注的,是人在動盪時代中的關係與認同。
就像是 「身分」 這個段落,始終在反覆追問:我們究竟是誰?
戲中的角色在政治與情感之間掙扎,而這場看似荒誕的鬧劇,映照的正是我們自身的困惑與拉扯。最終,快閃族4 用一條看不見的繩索拔河──一開始是兩群人對抗,到最後,竟成了一群人在與無形的力量對抗。
這是在和誰對抗呢?

昨天那個唱王菲大走音的女生,今天自殺了 #
在《亂民全講》眾多段落之中,「KTV」 或許是最耐人尋味的一個。這是一個近乎沒有政治訴求的片段,卻是整部劇情緒最飽滿、最令人不安的高潮。
場景設置得像是再普通不過的KTV包廂──一群下班的同事喝酒、聊天、唱歌,氣氛熱鬧。然而,在這熙熙攘攘之中,角落裡站著一名孤獨的女子。他站上椅子,拿著麥克風,唱著王菲的《紅豆》。聲音顫抖、走音,他的眼淚無聲滑落,而周遭的歡笑與談話聲卻絲毫不受影響。

當舞台上的投影幕亮起,一切變得不同。
「因為我已經決定離開這個世界」
「我坐在這個KTV房間裡,準備唱人生最後一次卡拉OK」
「你永遠也不會喜歡我」 「再也沒有任何感覺」
這些文字,像是KTV的跑馬燈歌詞,卻不是歌曲,而是這名女子的內心獨白。當他情緒越激動,背後的字幕閃爍得越快、越密集,層層堆疊的字句幾乎要將他吞沒。

這一幕讓人聯想到現代社群媒體時代的「彈幕文化」,但這些字幕不是來自觀眾,而是來自角色的內心世界,而台下的觀眾卻無能為力──甚至與包廂內的其他人一樣,對他的崩潰視而不見。
這名女子的歌聲近乎歇斯底里,卻在喧囂之中被完全忽視,像是一種無聲的求救。他的故事沒有清楚的交代,甚至沒有後續──我們不知道他最後到底有沒有自殺,就像我們在新聞裡常看到的社會案件,標題聳動,結局卻不了了之。
KTV 的孤獨 #
以結構來說,這段戲放在接近結尾的部分,是情緒最豐滿的段子,代表著是這場劇的重心與高峰,過了這段高峰便是結尾。
《亂民全講》的主軸,是政治諷刺,對民主、媒體、全球化、社會現象一一解構。但在眾多強烈批判的片段之中,KTV這段幾乎沒有主張,也沒有明確的政治隱喻,為什麼它會出現在這裡?甚至做為整部戲的高潮?
這正是這部劇最有趣的安排─它選擇了巨大的留白,而不是清楚的解答。選擇了情緒性極強卻毫無意見的段子,做為整部戲中轉折的核心,留給觀眾去詮釋。
可以非常感性地說「KTV」這一幕,它揭示了現代社會的本質,透過 KTV 熱鬧場景中的孤僻,暗示現代人在時代中的孤獨,雖然好似彼此融洽,卻在政治、思想、感情上與他人是遙遠的距離。
也可以用更後設的角度說,這是編劇的用意,在一個以政治搞笑節目「全民亂講」為諧擬命名的劇中,以一段只有感情,卻毫無主張的戲作為一切荒謬之下的收尾,反而更具有代表性。
但這些都只是我的腦補。
無論如何,它豐沛的情感,十足地帶給了觀眾震撼。整齣劇讓我最常回想的段子,便是這段刻意留白的 KTV。

越模糊,越有韻味 #
這段戲的留白,讓它擁有多種可能的解釋方式,這讓我想到台灣網路文化裡的「藍色窗簾」效應。所謂的「藍色窗簾」,指的是作者原本只是描述一面普通的窗簾,但讀者卻自作多情地賦予它各種隱喻:「窗簾是藍色的,代表主角內心的憂鬱與壓抑。」
我的解讀很有可能只是中了劇作家的設下的圈套,我也開始藍色窗簾了。
這正是劇場語言最迷人的地方──它不給你標準答案,反而讓你在文本的縫隙間尋找屬於自己的詮釋。
同樣的一場演出,每個人看到的、感受到的,都可能完全不同。
有人看見政治諷刺,有人看見社會冷漠,有人則只是覺得KTV那段很像某個深夜崩潰的朋友。
在這個短影音橫行、資訊碎片化的時代,影像作品越來越傾向「資訊爆炸」,用最快的方式告訴你「這就是答案」,而《亂民全講》作為劇劇史上的經典之作,它選擇「資訊留白」,讓你自己去找尋答案。
它告訴你,戲已經演完了,但問題還沒解決。
它告訴你,答案不是它來給,而是你要自己找。
這個時代,我們是誰?
這部戲沒有說破,但它已經把問題,完整地丟給了你。